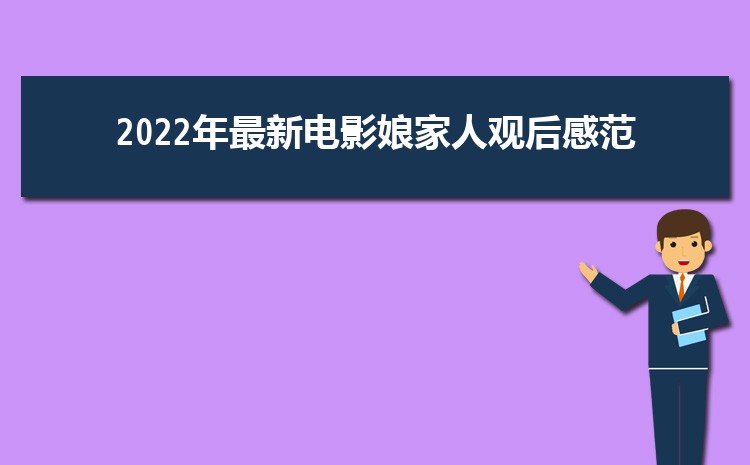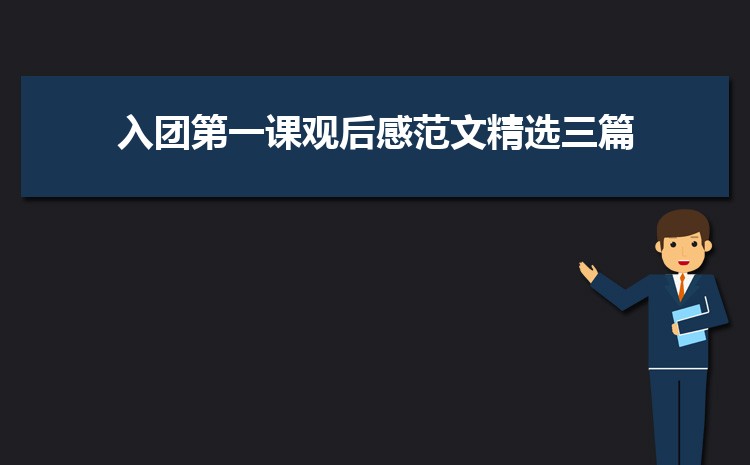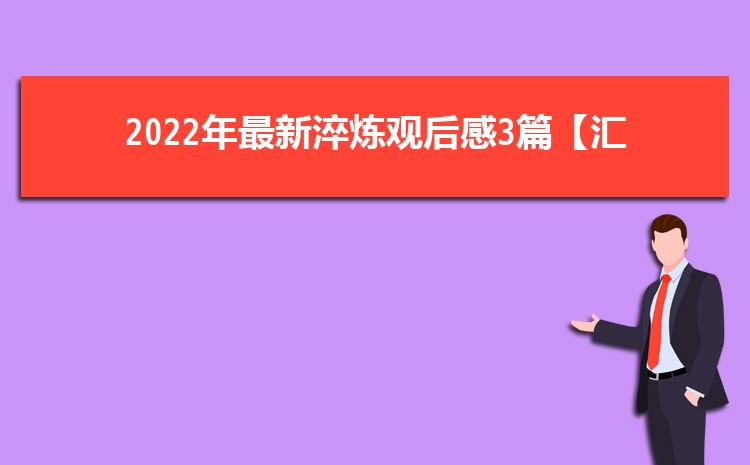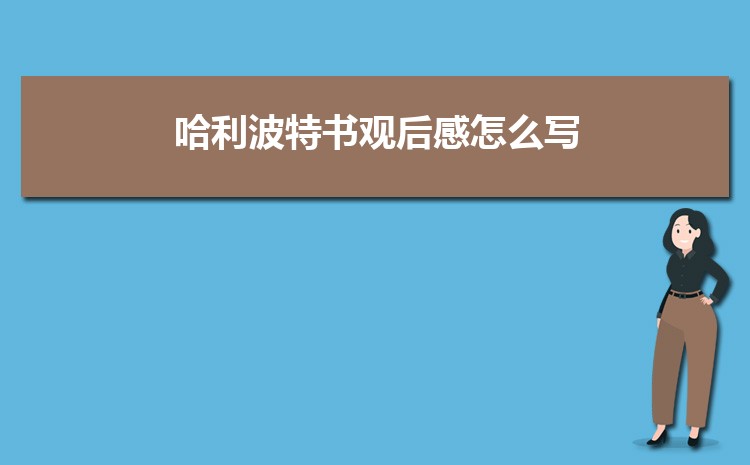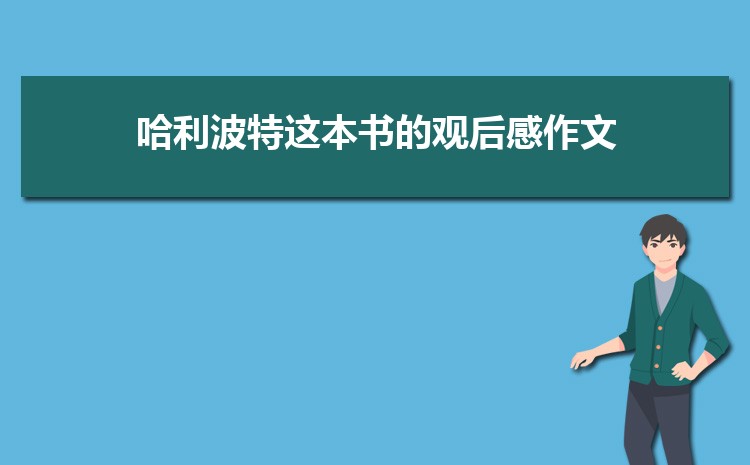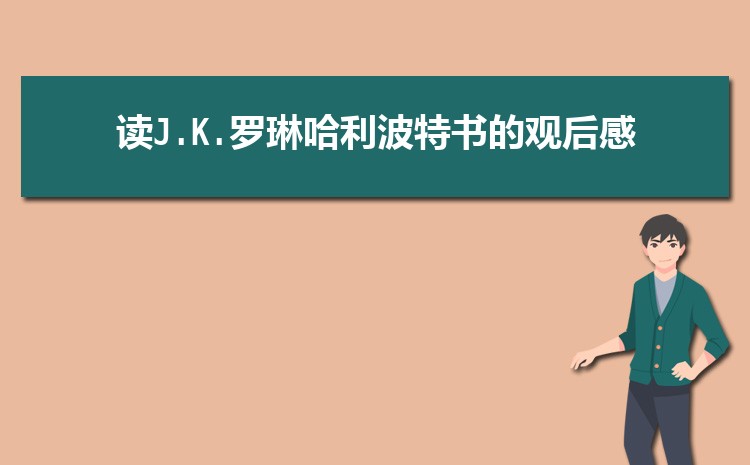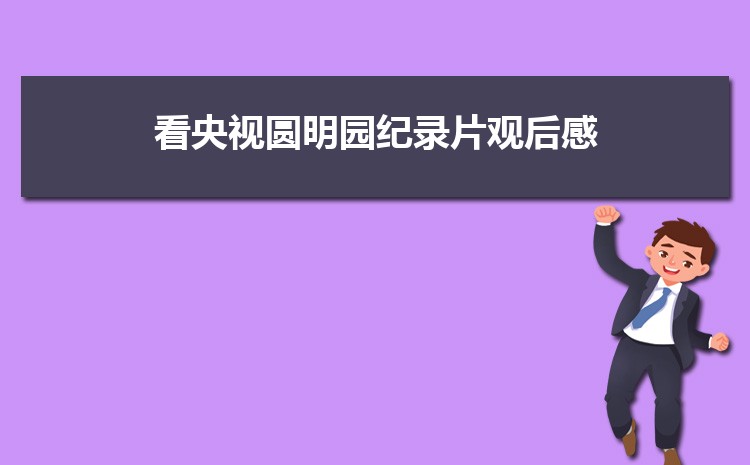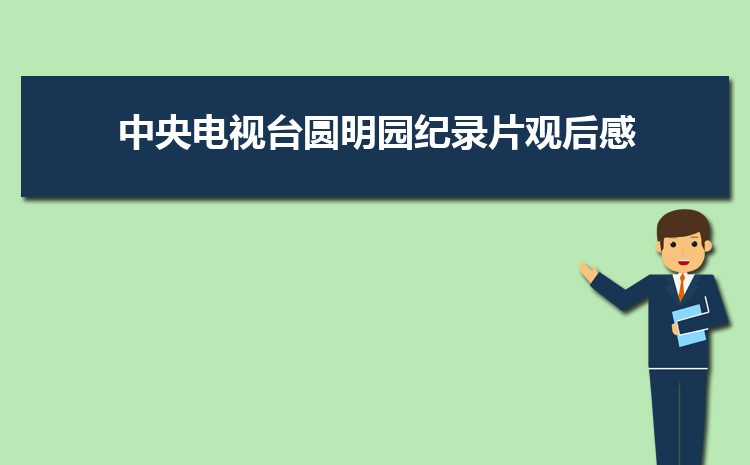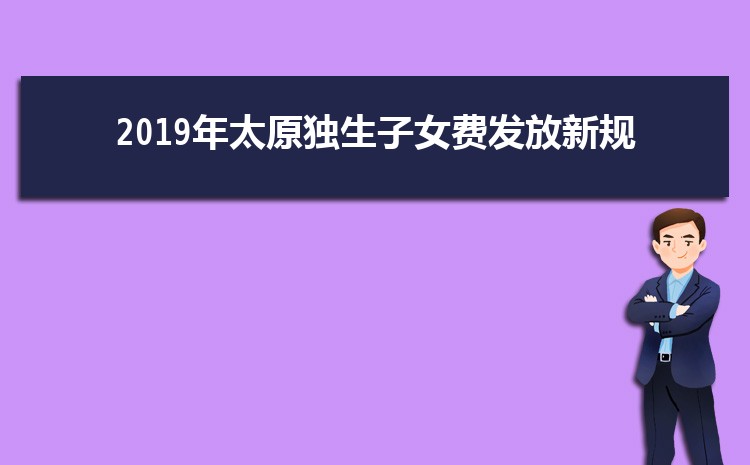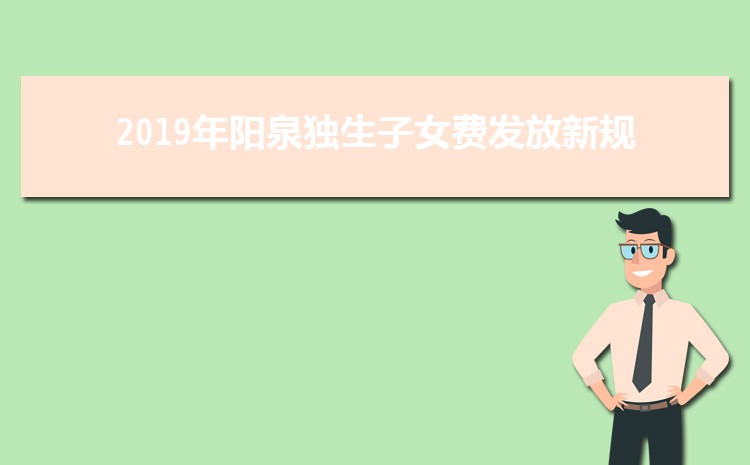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改编了这部电影。下面是华夏诗文网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喜福会》观后感,欢迎参考~
篇一:电影《喜福会》观后感
《喜福会》(《thejoyluckclub》1993),很老的电影,Gigi推荐,就抽时间看完,基本是连续着看完。
《喜福会》是一部关于女人的电影,是一部关于女人对幸福的追求的电影,是一部关于女人灵魂的自由的电影。
电影中人物很多,但是人物背后却始终是三种角色支撑:奶奶、母亲和女儿。奶奶在中国经历她的人生,母亲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女儿在美国长大并成家立业,三者连成一条完整的文化迁移链条。奶奶角色身上有非常强烈的晚清妇女观念残留:社会地位低、遭遇指腹为婚、在婚姻中永远处于弱势、自卑、容易满足、隐忍等等……然而她们表现的出的对自己女儿的爱,哪怕是在那个将女人当成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的社会中,这种爱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女人对自己骨肉的爱没有丝毫不同,没有丝毫的卑微。母亲角色因为战乱因缘际会来到美国,重新拥有家庭,开始另外一种文化寄居的人生,她们到老年的时候已经喜欢聚餐、抽烟、打麻将,讲着一口乎流利的美国英语,但是每一个在美国过着快乐晚年生活的母亲角色的背后,都深深埋藏着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关于婚姻的痛苦回忆。女儿角色已经是另外一块大陆文化的产物,她们只能在老照片里、书信里、或者他们的母亲的皱纹里才能稍微想象在那个遥远的陌生的国度里,有自己的根。
尼古拉斯凯奇在《战争之王》里的画外独白,让画面的魅力散发的更加彻底,在《喜福会》里也不例外。叙事线索的切换在大量旁白女声的连续中显得格外流畅,虽然线索很多,但是却梳理的很清晰。里面出现的种种文化符号,都或多或少让我们熟悉、震撼:农村妇女和富家女主人坐着定下自己幼小女儿的未来婚姻;母亲跪坐着紧抱自己淹死的孩子;“make a toast”式的ABC聚会;死者回魂观念对生者的威慑力;玉坠的代际传承;一夫多妻;没来由的性……绝大部分的符号,都在表现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所代表的价值和地位。
血脉亲情是电影表现的一大主题,但是电影还探讨了另外一个隐性主题:婚姻。虽然我没结过婚,好像说婚姻会显得自己很幼稚,也许本来就很幼稚。但是正是这样,我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婚姻这个东西。从电影里倒是不难提炼出婚姻的价值共识:尊重、沟通、理解、给彼此自由。毋庸置疑,在电影中,几乎所有女人的命运都是以婚姻为转折点的。奶奶角色在中国为人妻,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和自己孩子的性别捆绑在一起的,生儿子和生女儿将意味着母亲在婚姻中的方位千差万别;母亲角色来到美国,一边是自己在中国的残破婚姻,转过头来却还要寻找对婚姻的延续;女儿角色呢,则已经完全具备了美国婚姻观,男女间没有了敬畏和未知,他们交谈更彻底,却同时也为这种彻底付出代价。电影里出现的婚姻男性大都是强势、胜利者、不用承担责任和痛苦煎熬的角色。有人说婚姻中男女的地位的这种天生不等是以性为起点的,那就是说它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探讨可以写本书了)它甚至直至今天仍然强烈的影响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讨论未来时不自主所具备的立场……女权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滥觞也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我个人仍然坚持男女等。婚姻是一个旅程,我们规定了和期望着它要和生命同时走到尽头,所以在开始旅程时我们总要满怀信心。
曾梅最后见到自己两个孪生姐姐的镜头,昭示着叙事链条的首尾相接,算是圆满的结局,她的姐姐梗咽着喊出“妹妹”的时候,我也跟着梗咽。女人的灵魂自由有多么重要,现在又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一点呢?
篇二:电影《喜福会》观后感
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改编了这部电影。
一部电影讲述八位女性的故事,能如此从从容容,也是功力。块状的结构略显庸,可是至少每个女性的面目是清晰的。这八位女性,她们的生命都与东方,准确地说是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在这部电影中,对于四位母亲来说,是一个需要在现实空间中逃离的场所,赴美之旅使她们自我“解放”的起点;对于四位女儿来说,是一个需要在心灵空间上逃离的场所,她们需要不像她们的母辈那样活着,在内心上强大起来。就这样,女性的解放和对中国的脱离被并置。
我认为,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观点,还是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弱者”永远是被书写和被塑造的,他们没有自我言说的机会,于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成为“他者”。(这里的弱者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里为了概括方便,选取了一种惯常的说法,其实他们??无论是女性还是东方社会??很可能并非事实上的“弱者”)这种概括当然无法囊括两种理论的丰富性,但是却能从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两种理论的相似内核。而因为如此,东方女性便更加边缘。这部电影中,女性形象与中国影像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于是本文将利用女性主义和对东方主义的反思观点,来分析本片在塑造女性角色和描绘中国图景之间所出现的观念的不同步。同时探讨这种不同步的两种观念如何互相牵制,使得两方面都出现了即进步又保守的含混表达。
一.女性主体性的建立
小说原著作者是女作家谭恩美。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使得小说《喜福会》成为一部典型的女性文本。王颖虽然是一位男性导演,但在这方面,对原著的遵守做的比较好(也许是谭恩美参与编剧的缘故)。主角是八位女性,但事实上片中所揭示的女性寻找自我的历程不仅只发生在这八位女性身上,还包括安美的母亲(邬君梅饰)和林多的母亲(奚美娟)。于是这种历程跨越了三代女性。影片通过叙事和影像的处理,塑造了这样一个女人的世界,这些女性像天鹅羽毛那样柔弱,却完成了漂洋过海的自我肯定的过程。
首先,无论在叙事上还是影像上,父亲都是缺席的,或者刻意被省略。四位女儿的任何一位父亲,甚至四位母亲的任何一位父亲都没有进入叙事主线。他们不是女儿的精神支柱,也非崇拜的偶像。甚至于危机之中拯救女儿的,也是母亲。父亲们处于景深出,是一个模糊寡言的身影。君的父亲在结尾处的戏,也是承担了讲述君的母亲的过去的任务,成为母女之间精神延续的一种桥梁。这个父亲是矮小的,有些畏缩。父亲的缺席,凸显出母亲的重要,使得这种独立精神的传承有了母系的,使得女性解放的路成了一条自救的路。
这个喜福会,也一直是君的母亲操持的,或者说是由那四位母亲所支撑着。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处理,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安东尼娅家族》中,人们总是开心地在安东尼娅家的院子里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母系社会建立起来。喜福会与此异曲同工。都是女性维系了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人们情感的归宿,是人们对抗疏远的武器。虽然里面仍然是家长里短,女性的工作无非是准备食物,可是琐碎的工作是社会的基石。
里面的女性从忍辱负重的典型东方旧女性,到试图割舍过去的美国新女性,每个女性都有不同的面孔,似乎勾勒了一幅女性解放历程的图谱。安美的母亲用死亡的方式让安美觉醒,这个代价是巨大的。而盈盈通过溺死自己的儿子这种自虐式的方式换来自身的自由,并经过漫长的一生将这种对尊严的追求落实到女儿身上。母亲身上所经历的或者是背负的对两性关系的不堪回忆以及采取的极端行为,使得女儿们终于能以较为和而理性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婚姻,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像罗丝仅凭一席话,就重新得到了丈夫的心(当然,影片对这位“白马王子”的刻画过于完美了)。
虽然也许是由于原小说的缘故,有些话语过于直白地表达出来,略显教条。另外,电影对父权的揭露,也流于简单直接。但创作者总是在努力建立女性的主体性。无论是由女性讲述的旁白,还是围绕女性展开的回忆,都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中国”主体性的丧失
用“丧失”也许不妥当,因为在东方主义阴影下,东方都不曾成为过主体。谭恩美是移民二代,生于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或许只能来自长辈的讲述,或许带着和西方人一样的窥视、探秘心理也未可知。
而由于导演王颖本身的身份特殊性,影片对中国的描述,就体现为一个华裔导演按照西方对中国大陆的想象,塑造了“中国式的”形象和“中国式的”故事。导演作为华人判断力失效,转而用西方的标准来塑造形象、讲述故事。于是影片中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充满了符号性的元素。无论是事件本身、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的刻画,都极大程度地“典型化”了。
这些故事包括了童养媳的故事,她有个不懂事的小丈夫和邪恶的婆婆;也包括了寡妇再嫁的故事,她成了姨太太,再嫁遭家人唾弃,吞鸦片自杀;还包括苦命女学生的故事,本是进步女性,可是嫁了不良老公,遭虐待。这些故事在中国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几乎快可以被称为“原型”了。但是放在大陆的影视作品中,并不别扭。原因是,只有“原型”并不够,只有做到细枝末节都像才行,最关键是人物的心理逻辑要正确,最起码应该是中国人的心理逻辑。可是这些个典型故事放在一部电影中,展览般演开去,别说西方人了,我相信连中国人看了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为了都展览完,也便不太顾及人物的心理反应逻辑了。比如林多作为童养媳,娘家人搬到了南方,应该就失去联系了,一个小女孩怎么就敢毅然决然地要出逃了?况且那个关于祖先的谎撒得绘声绘色,苦出身的林多怎就见得比大户人家的人更聪明,她不怕祖先真的来惩罚么?她竟是无神论者了?其他几个故事也一样,旁白不断进入叙事,试图加快叙事的速度,建立人物行为的心理依据,但逃不脱俗套情节一股脑地加入。这些故事,映衬了西方对东方愚昧落后的想象。当然,这些或许都是事实,真实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可是,就像报纸上所有真实的新闻最后可能拼凑成一个巨大的假象一样,这些事实建构出来的,也只能是局部的中国??可却很可能是全部的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
还有那些符号性的人物:童养媳、姨太太、恶婆婆、脸谱化的媒婆。还有那些神秘的东西:关于鬼魂的诅咒,割肉救母的疗法……中国成为景片,一页页翻过去,琳琅满目。在这里,中国便任人书写了。或许,无论对于谭恩美或者王颖而言,关于中国的记忆就是这样一张张景片了,就像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林多的妈妈??奚美娟扮演,一张朴素的典型的中国女性的面庞,出现在一块小方镜中。四周是漆黑一片,镜子中的脸上,印着昏黄的灯光。
三、混沌的讲述
前面提到,由于创作者关于女性与东方的持有错位的观念,造成了电影叙事上的含混。女性与中国,同为边缘的个体,一个具有走向自我的确立,一个更加陷落。女性的主体性的确立以逃离中国为前提。(尽管那是“旧中国”,或者“古老中国”。可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很多就是个“古国”,我们是文明古国,人家自动去掉了“文明”两字。)于是,女性的这种解放便可以被提出质疑,她们的逃离会不会是另外一种落网呢?究竟是她们自救还是美国拯救了她们?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解放到了何种程度,她们这种逃离意义何在呢(单就女性地位来衡量)?对于女性主义而言,经由这种方式来得到自身的解放,与改变女性现状无益,她们无非是由一种粗暴的父权社会,进入一种相对文明的父权社会。她们的主体性程度,取决于所处社会父权程度。同为帅气的富家少爷,盈盈的年青时的中国丈夫花心、残暴,而罗丝的丈夫彬彬有礼,在罗丝敢于表达自己之后,重新爱上了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别忘了他也是出过轨的。
同样,对于中国,创作者的态度也是混沌的。每个女性,尤其是母辈,都无法消除中国留给她们的影响。最有趣的设置是君和她的母亲。君一直未婚,而且似乎各方面都不太成功。可是她最终来到中国,和双胞胎姐姐团聚,她没有丈夫可是却更能体会家的概念。而此前,我认为本片最有意思的一句台词也用在她身上,林多对君说:“你们美国女孩儿一定认为,中国人、犹太人,有什么不同么?”这是对东方主义的一个小小挑衅。它告诉美国观众,中国有自己特点,遗憾的是本片却并没有提供什么积极建设。可最终是这个“美国女孩儿”,回到中国。影片开始照合照,缺少君的母亲,而她最后出现在中国,和她的一个女儿站在一起,虽然那是君的幻想。可是,这似乎说明这些女性生命中总有些残缺,那残缺,是对中国的记忆。创作者表达出了文化融合的期望。
这部电影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可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便呈现出有趣的复杂性。小说《喜福会》使得谭恩美在美国声名鹊起,电影《喜福会》使得王颖得以进入好莱坞。无论是女性,还是中国,都需要自己的讲述者。尽管这样的讲述者,也许依然无法摆脱男权或者东方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