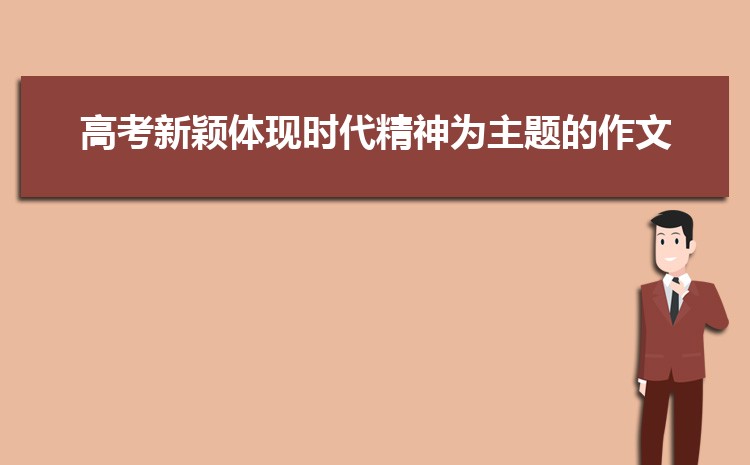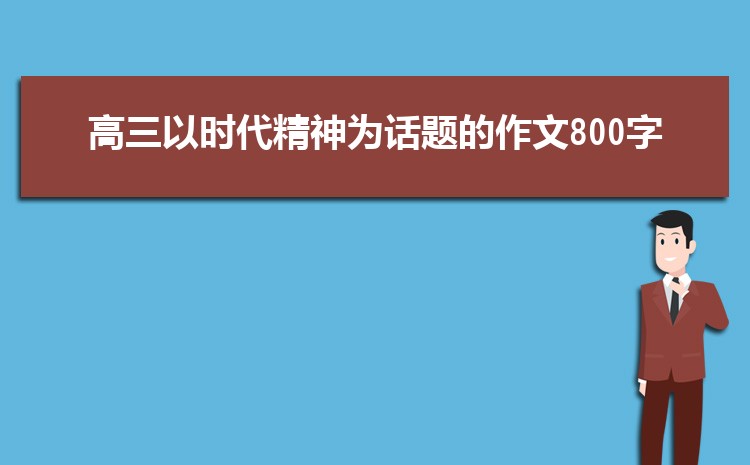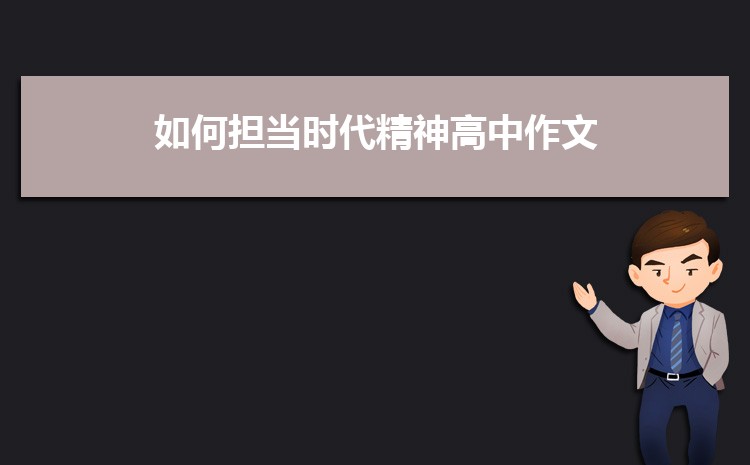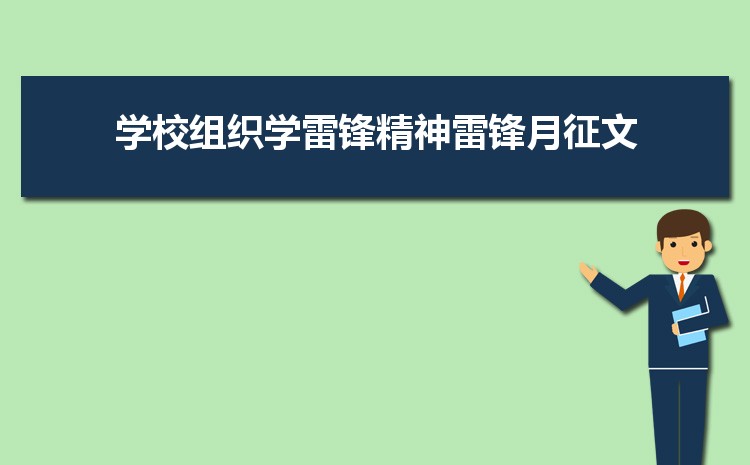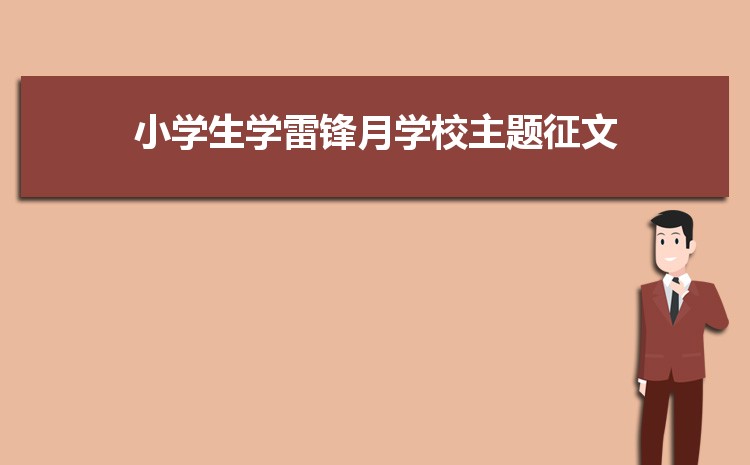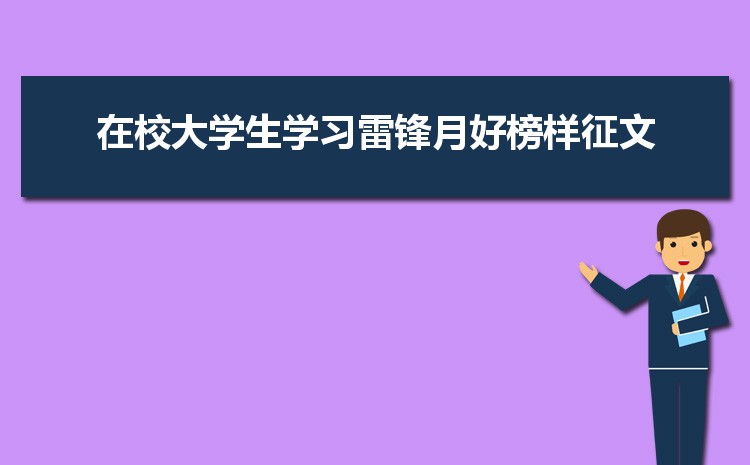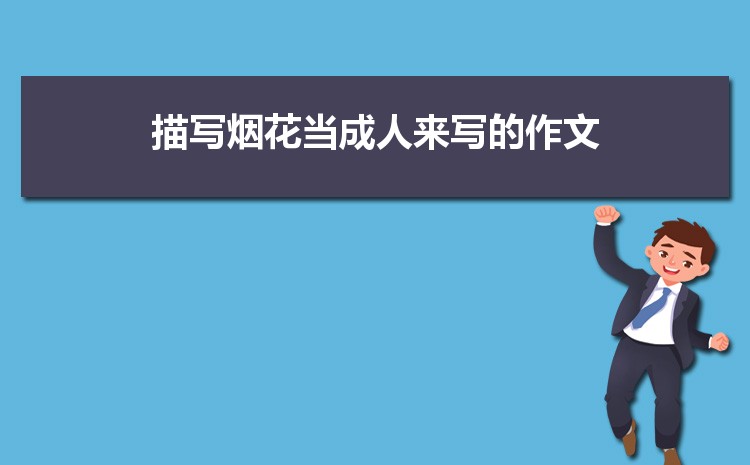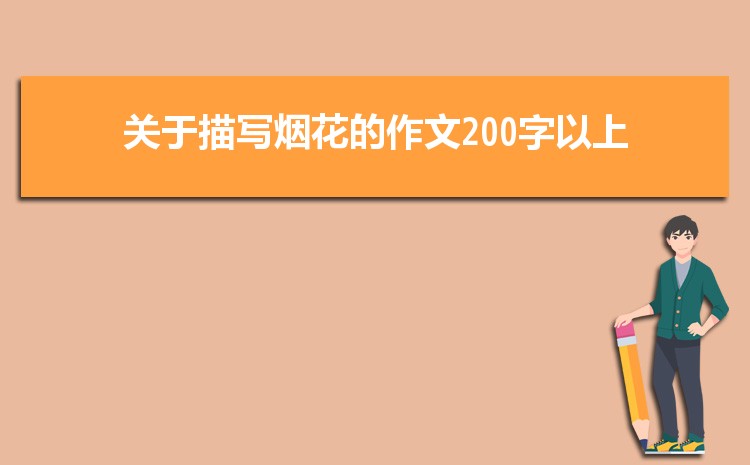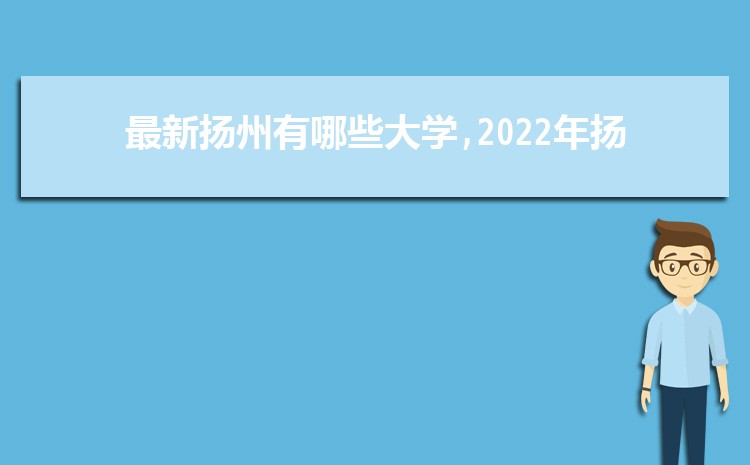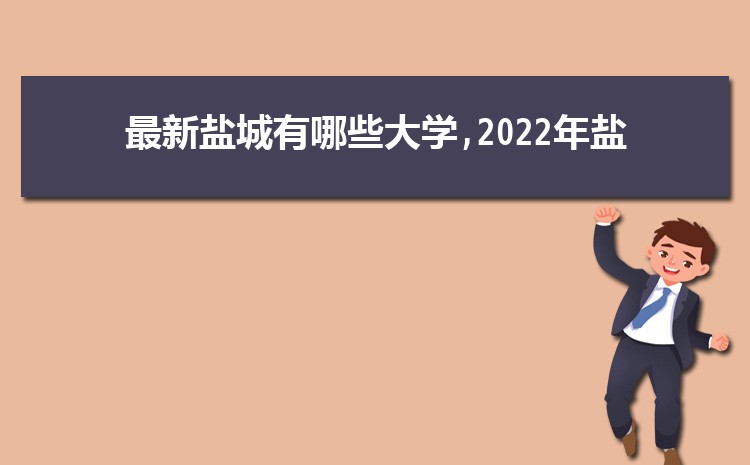篇一:答案在风中飘荡创新作文
男孩独坐在床头,秋风把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头的的黑夜吹来,压在他心头上。他是一个失去了“生命”的琴者。
凭什么?
不管是论天赋,还是论努力,他无疑是团队里最优秀的。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七岁的时候因一场病他错过了向更高水团队晋升的机会,今年他十四岁,为了这再一次的机会,他不分日夜地努力着,又一场意外毁了他的左手,那几乎是他的生命。
凭什么?
于心自问,我日日夜夜的努力着,我天赋卓越却从不浮躁,为什么却只有我的付出得不到等价的回报,而那些……顶替我的人,他们没我聪明,他们没我努力,他们每天玩几个小时的游戏我碰都没碰过,他们放弃的难曲子我都咬着牙克服,凭什么那些人就运气那么好,我却要看着一群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人纷纷登上本该由我登上的舞台?那些人,那些除了运气什么都没有的,那些……那些蠢货!
“混蛋!蠢货!渣渣!”
他没能克制住,直接把心里骂人的话喊了出来。而后他双腿颤动,脑袋乱晃,脸上的肉把周围的空气颤成了一层一层的波。珠状的液体挤在眼眶里,被他以强烈的吸气抑制在眼眶里,他的脸憋成了苹果红。
他已经几个月没有碰过小提琴了。自从有一天他突然发狂,撕掉了自己所有的书,甚至已经把小提琴举到自己手里准备摔下,而后的一瞬间眼泪珠子刷的一下掉到地上,他手一松,整个人连同小提琴一起倒地,在一片刺眼的阳光下满房间的碎纸屑反射出金光,在一地碎屑中他抱紧了小提琴,把脑袋深深地缩进臂膀,缩成一个不见光的黑点,他无力的抽泣着,眼前有一大片黑暗,身旁还有浓浓的雾,他要怎么走以后的路?
妈妈一回家就紧紧地抱住他。“不拉了,我们不拉了。”
这几个月来他在家里看电视,玩游戏,不断麻木着自己的神经,极力回避着心中那一个问题:我是否要放弃?
这天深夜他接到教练的电话。“把你从小到大,拉小提琴得的所有奖带上,跟我来。”
“无非就是要我做个了断什么的,断就断,谁怕谁啊”,他一边爬山一边想着,但是爬山的脚步终究是慢了一些,拖拖踏踏不情不愿。教练的声音在耳边传来:“快点!婆婆妈妈的,怎么,舍不得?”
他犟嘴道:“谁舍不得了?风带大了!”说着他抬起头来,山风特别给他面子,一下子大起来,掀掉了他头上的帽子,打在他的额头上,在他耳边呼啸而过仿佛夹杂着千言万语。
他们终于爬到了山顶。
在教练叫他拿出那一张张奖状,一尊尊奖杯时他的心里还是免不了“咯噔”一下,但他还是咬咬牙狠狠心撕掉了所有的奖状,此时的风更大了,他多年奋斗的成果一下子就没影儿了,消失了,头发贴在他的脸上,他的脸是颤抖的。
教练拿出他的一座奖杯,“扔了!”
他的声音仿佛被风割成了碎片一样,“奖杯扔下去,砸到人就不好了。”
“叫你扔你就扔!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人!砸到人我负责!”
他在教练的吼声中扔下一个又一个奖杯,风是那样的紧紧压迫着他,他每扔一个奖杯时风都几乎连着他一起吹下悬崖。此时风已经很大,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连方向都看不清楚了。他接过这最后一个奖杯的双手已经抖的快要接不住了,他站在悬崖边上,屡次伸出手又缩回手,快被风吹倒又被风扶起。“快扔!”教练的吼声仍在耳边,他终于忍不住大哭大喊起来:“不扔了吧,就剩这一个了,不扔了吧!”
四岁的时候他对小提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到周末就抱着小提琴风雨无阻地去上课。他总是班里的佼佼者。
五岁的时候碰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拉不出来的曲子,他没日没夜地练着,终于克服了难关。
七岁那年在全省最好队伍的选拔中一路过关斩将,却因为一场大病错过决赛。他废寝忘食地训练,终于进了那支队伍。
八岁的他发现一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他没有气馁,再次凭借努力赶上队友。此后的一年一年,他拉着小提琴,度过了那么多快乐而充实的日子,赢得荣誉无数,每一尊奖杯后都洋溢着他的笑脸。此刻他的笑脸,他抱着提琴去上课的身影就在风中,就在他眼前,他怎么可能视而不见,他怎么能扔掉这最后一座奖杯,他根本忘不掉,他根本放不下!他终于被风吹垮了,跌坐在石崖上仰面大哭起来。
“下不了手了吧,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教练轻轻走到他旁边,“孩子,你不能不信自己,你能重新进入省队,还跟上了落下整整一年的进度,你怎么就不能重新打入国家队?只要你想,我就能把你带进去,有什么可怕的?你有天赋又努力,不过是少了点运气,能怎么样呢?再说让你感到快乐的是拉琴本身不是吗?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到底要不要放弃?”
他大声的喊:“不放弃!我不放弃!我要继续!”山风割面如刀,男孩带着哭腔的声音却头一次如此坚定有力得穿透了如千沙呼啸万石狂滚的风。在风的切割解剖之下他如此清楚的看清了自己,就是从风在他耳边掐着秒和他一起喊出答案的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男孩了。
一个男人成为一个男人之前走过各种各样的路,并不是每一次淌过沼泽都离成功更一步,但是没有一个男人因为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而放弃过,只因为泼洒过的汗水已经在土地里,总想看看再付出一些是不是就能收获。而他挥洒过的汗水的味道由风记录,每当他回头的时候风见证着他的努力,他的成长。他其实一早就知道,从风开始在他耳边呼啸的时候就知道,还有什么可挣扎的呢?答案早已在风中飘荡。
篇二:答案在风中飘荡创新作文
风起时,吹皱一池春水。
从记忆中那座小桥说起。最早的那座桥是青石板搭成的,桥面散发着湿冷的幽青。参差地叠在一块儿的石板缝隙边上偷长了好几片零星的青苔,放肆地点缀在桥面之上,诉说着时光的无情和岁月的沧桑。桥上坐着一个扶着二胡的男人,由桥面空气抖动弥漫在湿冷空气中的琴声,属于这个男人。
男人年纪不算老,约莫四十出头的样子,削瘦的脸上只挂着一点作为人的皮肉,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在骷髅眼里,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翳,他两只眼睛都不知害了什么病,瞎掉了,周围一些老一辈的人捉摸他年轻时可能不检点,以致害了这种怪病,于是好容易能让这份干瘪的躯壳出现一点生机的器官也没有了,一天到晚倒腾个白眼珠子。配上尘世尘土落满的黑发,活像是梁正英片子里的那些僵尸。
瞎子的来历很神秘,老一辈的那些整日爱挤在老人院和麻将谈天说地的胡同老炮儿大妈也不晓得他的来历。我猜想可能瞎子像古龙小说中那些深藏不露的高手一般在白雾连山的清晨,孤独地背着他那把比他更具沧桑的二胡来到我的这座小山村,寂寞地演奏一代大侠多少年江湖上的腥风血雨。
而事实上,瞎子这么多年来演奏的究竟是什么曲目,我至今仍不知道。
江南的乡村醒得很早。一笼蒸气冲开蒸笼盖顶时,乡村就睁开了眼。几番人来人往,老瞎子的二胡声就开始在晨曦中飘散开来。远处,几座永远衔着白色云雾地连绵在一起,夹杂着水汽的微风一吹,太阳千军万马的芒刺破了军。随后,乐村就醒了过来。
他大概是躺在黑夜之中,所以夜的末梢一消失,二胡声就飘起来了。瞎子坐在桥头的边上,手扶那把耷拉着琴弦的二胡,眯着眼,干枯的手指节间断反复地按压在头上的弦上,打满了灰尘的小腿上绑了一块木筒拉到转合处,他踩上一脚,木筒“当??”一声,完成了合奏。
他一天都如此尽心尽力地演奏,位置前摆着一个空碗,里面孤零零地躺着零星几个硬币。瞎子动作辐度极大,头经常是一甩一甩的,过来的人觉着有意思,围过来听听,但不一会儿又回去忙活自己的事了,能给瞎子钱的人并不多。直到绛紫色的黄昏来临,瞎子碗里的总数也不见得有涨几个。
我的家离那座桥很,似乎迈个几步就能到的样子。那个时候桥上没有车,周围又都是认识的人,所以跑去桥上玩,家里人也不会太在意,反正吃饭时呼一声,就有熟人拎着我回来了。
我跑到桥上,思考桥面上那个拉二胡的男人是否也有如扫地僧一样深厚的功力。我太欣赏这种英雄一般神秘的人了,但镶在石板上佝偻的身体又向我诉说着恐惧。“我真的能白无故地过去听他拉二胡吗?”我反复地问着自己。然而在偶然得到一角硬币后,我终于可以有正当理由走他了。
我惴惴不安地揣着一角钱小心翼翼地拨开桥面上的人在他碗里放了一角钱。“咣当”我的心停住了,瞎子也似乎愣了一下,琴声也随之凝固在空气当中,继而努力地向我点头示意。我小心地望着那具干枯的躯壳,大侠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仔细打量起瞎子,乐村里带着粗砾的风在他身上刮了一年。他一身袍,又加些有的没的搭缀,破外套,上下应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着色。不算太臭,脸也不脏,一双眼珠色极浅,且浑,好像又不是全瞎。它们像蕴满了云的天空,你没有注意时,它是一动不动,仿佛布景,但当仔细凝视时,就会发现它们以一种你不能理解的运动形式思考着和游走着。除了琴声,他还是一无所有。
二胡的琴声随风婉转悠扬,乐村里的他也有快乐吗?
逐渐乐村经济发展起来了。那座桥由于更大的用途被翻了新,可以通车了。翻新时,桥上的所有东西也都随着机器的轰鸣消逝在了无尽的微风之中。
聚散由天,村里老人说。
瞎子带上他的二胡,不知踱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去了别村拉二胡。总之乐村人再也没见过他。说起他,就说起桥。说起桥,就又说起了,没了故事和没了琴声。
他去向了何方?那琴声又飘去了何处呢?